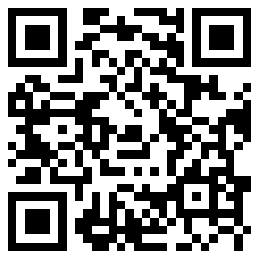陪葬墓
4、陪葬墓
内容出自《西汉十一陵》作者刘庆柱、李毓芳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
(一)陪葬墓的分布
据文献记载,陪葬于茂陵的有卫青、平阳公主、霍去病、金日磾、霍光、董仲舒、公孙弘、李延年、上官安、上官桀、敬夫人,以及京兆尹曹氏等。此外,象大侠原涉这样的豪杰也在茂陵“买地开道”、“治冢舍、奢僭踰制”【《汉书·游侠传》卷九十二,第3716、3118页】。关于这些陪葬墓的方位,有的文献记载比较具体明确,如卫青、平阳公主、霍去病、霍光及上官氏家族等。其余则不太清楚。茂陵陪葬墓主要分布在茂陵以东,陵园东司马门道的南北两侧。地面现存封土的陪葬墓共12座。从布局来看,可以分成四组:卫青、霍去病、金日磾墓和六号墓为一组;一、二号墓为一组;七、八、九、十号墓为一组;霍光墓和第十二号墓为一组。前两组在东司马道北侧,后两组在东司马道南侧。
(二)陪葬者及其墓葬的位置
卫青,字仲卿,河东平阳(今山西临汾西南)人。其母系平阳公主家的奴婢,与郑季私通而生卫青。卫青长大后,成了平阳公主的家奴;他的同母姐姐卫子夫得幸于武帝。因而,卫青被汉武帝重用,封为长平侯,官至大将军。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,汉武帝派卫青率领部队与匈奴作战,控制了河套地区。不久,他又与霍去病一起打败了匈奴主力。卫青前后七次出击匈奴,斩首虏五万余级,保卫了西北边陲的安定,解除了长期以来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。由于战功卓著,他姐姐又是武帝的皇后,因而“尊贵无比”。后来,卫青与其青少年时代的女主人――平阳公主成婚。卫青死后,陪葬于茂陵。卫青墓在茂陵以东900米,是离茂陵较近的陪葬墓之一。该墓坟丘形如庐山。庐山亦名颜山,系当时匈奴辖境内的大山,卫青曾在此立下赫赫战功。把卫青墓修成庐山状,是对卫青战功的纪念。卫青的墓冢,底部南北95米、东西70米,顶部南北18米、东西4米,冢高21.4米。
霍去病(公元前140年――前117年)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青年军事家。家居河东平阳。他是霍仲孺与卫少儿的私生子,卫少儿是卫青和孝武卫皇后(卫子夫)的姐姐。霍去病仰仗其姨母,很快得到朝廷重用。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,他率军两次打败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,控制了中西交通的孔道――河西走廊。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霍去病又与他舅父卫青击败匈奴主力部队,赢得了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决定性胜利。霍去病在六年军事生涯中,六次出击匈奴,屡建奇功,保卫了西汉王朝的边境安全,开辟了名垂青史的“丝绸之路”,为中西文化交流披荆斩棘做出了卓越贡献,被汉武帝封为“冠军侯”,官至骠骑将军,秩禄与大将军卫青相等,名望甚至超过了卫青,因而卫青许多部下纷纷投奔霍去病。汉武帝在京师长安为他建造了豪华的宅第,他却说:“匈奴不灭,无以家为也”。元狩六年(公元前117年),霍去病去世,年仅二十四岁。汉武帝下令霍去病所征服的边境五郡派出将士代表,身着黑铠甲,又在长安与茂陵之间,布成东西几十里的军阵,夹道为霍去病送葬。霍去病墓修在茂陵东边,西邻卫青墓。“票骑发迹于祁连”【《汉书·扬雄传》卷八十七[下],第3573页】,为了纪念霍去病在祁连山一带抗击匈奴侵略的丰功伟绩,霍去病墓的封土建成祁连山的形状。封土上堆放着巨石,墓前陈列着石人、石马、石虎、石象、石牛、石鱼等组成的大型石雕。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92米、东西61米,顶部南北15米、东西8米,冢高15.5米。
金日磾(公元前134年~前86年),字翁叔,系匈奴休屠王的太子。《汉书·金日磾传》记载:“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,故因赐姓金氏。”霍去病对匈奴战争取得节节胜利,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出现严重分歧。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共同约定投降汉军,但休屠王改变了主意。昆邪王杀了休屠王,率部分匈奴军队投降了西汉王朝。金日磾和他弟弟金伦、母亲阏氏被西汉王朝收纳官府作为奴隶,饲养马匹。金日磾忠于职守,颇得汉武帝赏识,先后被任命为马监、侍中、驸马都尉、光禄大夫。汉武帝不因金日磾是少数民族、又是反对过自己的匈奴首领之子而歧视、疏远他,而是根据他的德行“贵重之”。金日磾在粉碎莽河罗刺杀汉武帝的阴谋活动中立了大功,被武帝封为侯。武帝死后,金日磾和霍光一起铺佐昭帝。金日磾死时,皇帝“赐葬具冢地,送以轻车介士,军阵至茂陵”【《汉书·金日磾传》卷六十八,第2926页】,陪葬于武帝茂陵之旁。金日磾墓在霍去病墓东邻,形如覆斗,冢底部长41米、宽36米,冢高11.2米。陈直先生认为此墓为大行李息墓【陈直:《汉书新证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,第322页】,但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记载来看,李息在朝廷为官政绩一般。后来汉武帝追究张汤自杀一案,又涉及到李息,并免去其“大行令”,让他陪葬在霍去病墓东邻的茂陵陪葬区这个显赫位置,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李息陪葬于茂陵之说恐难成立。
霍光,字子孟,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。霍去病在京师当官后,把年仅十几岁的霍光带到了长安。武帝任命霍光为侍中。以后他又相继出任奉常都尉和光禄大夫。由于霍光在汉武帝身边“出则奉车,入侍左右,出入禁闼二十余年,小心谨慎,未尝有过”【《汉书、霍光传》卷六十七,第2931页】,所以深得信任。汉武帝晚年,霍光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,“受遗诏辅少主”。汉昭帝即位时才八岁,朝廷“政事壹决于光。”后来,霍光的外孙女又被召入宫,并册立为皇后(即孝昭上官皇后),霍光的地位更加显赫。昭帝死后,他又与朝廷群臣废掉即帝位的昌邑王刘贺,拥立皇曾孙刘询为帝。霍光是三朝元老,从政达二十年之久,地节二年(公元前68年)去世。汉宣帝亲临哀悼,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:由“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。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。赐金钱、缯絮、绣被百领,衣五十箧,璧珠玑玉衣,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各一具,枞木外臧椁十五具。东园温明,皆如乘舆制度。载光尸柩以輼輬车,黄屋左纛,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阵至茂陵,以送其葬。”在茂陵东边,“发三河卒穿复土”,为霍光修建了坟墓和祠堂。“置园邑三百家,长丞奉守如旧法”【《汉书·霍光传》卷六十八,第2948页】。茂陵以东4000米,兴平县西吴乡陈阡村有今传霍光墓,墓前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的碑石。墓冢底部长72米、宽64米,高19.5米。近年来,在该墓以东500米曾发现大面积西汉时代的建筑遗址,还有部分壁画遗迹,以及云纹和文字瓦当。其中出土的“加气始降”、“屯泽流施”、“光由宇”和“道德顺序”等文字瓦当,为过去所少见。霍光生前预作寿墓,其茔制已经超过规定。霍光死后,他的妻子“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面侈大之。起三出阙,筑神道,北临昭灵,南出承恩,盛饰祠室,辇阁通属永巷,而幽良人婢妾守之。”【《汉书·霍光传》卷六十八,第2950页。】由此可见其坟茔、祠室、园邑规模很大,而且其中不少是照当时皇帝葬仪的规格营建的。
董仲舒(公元前179~前104年),广川(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)人,汉代哲学家,自幼攻读儒家典籍,景帝时为博士。建元五年(公元前136年),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尊崇孔子的学说,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,抑黜百家,独尊儒术,确立了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。在教育上,他主张立太学,设庠序;在人事制度方面,提出州郡举茂才孝廉,开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科举之先声。董仲舒在朝廷当官后,家徙茂陵邑,年老时“去位归居”于此,后在茂陵邑家中去世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七记载:“董仲舒墓在县(兴平)东北二十里。”今兴平县南位乡策村东南250米,茂陵东北652米有一墓冢,当地群众称“次冢”,相传为董仲舒墓。此冢底部长71米、宽30米,冢高14.3米。
公孙弘(公元前200年~前121年),字季,原籍菑川,家居薛县。年轻时当过狱吏,后因罪免职,家境贫寒,四处流浪。年近四十,方才学习“春秋杂说”。六十岁时,“以贤良徵为博士”,后又任内史、卸史大夫等重要官职,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年)公孙弘任丞相,以八十高龄死于任上。汉武帝对他评价很高,认为“汉兴以来,股肱在位,身行俭约,轻财重义,未有若公孙弘者也。”他虽“位在宰相封侯,而为布被脱粟之饭,奉禄以给故人宾客,无有所余,可谓减于制度。”【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卷五十八,第2624页。】公孙弘死后陪葬于茂陵东北约一里处。
李延年,生卒年不详,中山人,出身于梨园世家,由于犯法而被处以“腐刑”,遣送到皇帝的养狗场(狗监)做工。李延年不仅是个出色的歌唱家,而且还是个杰出的作曲家。汉武帝为祭祀天地所编的大量歌曲,就是由天文学家司马相如写词,他谱曲。后来,他凭其妹李夫人之势,官至协律都尉,“佩二千石印绶”,深得武帝宠爱,“与上卧起”【《汉书·佞幸传》卷九十三,第3726页】。李夫人死后,李延年也逐渐被疏远,后来全家被诛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七记载:李延年墓在兴平县东北18里。
上官桀,陇西上邽(今甘肃天水)人,青年时期曾为武帝随从中的羽林、期门郎,因其力大无比,被武帝任命为未央厩令(皇官中的马官)。由于得到武帝常识,很快晋升为侍中,官至太仆,后又为左将军,被封安阳侯。武帝晚年曾遗诏,由霍光、金日磾和上官桀“辅佐少主”。后来,霍光把女儿嫁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。上官安结婚后,生一女儿,就送入皇宫,进为婕妤。过了一月,这个年仅六岁的小女孩被立为皇后,即孝昭上官皇后。上官氏父子横行朝野、穷奢极欲,并策划废掉昭帝,谋杀霍光。事情败露后,上官氏宗族被夷。上官皇后由于年幼,未参预她父母和祖父的阴谋活动;又因她是霍光的外孙女,所以未被株连。上官皇后的母亲(即霍光女儿)敬夫人,在上官氏被灭族之前已死去,葬在茂陵以东,大概在霍光墓附近。敬夫人墓附近“置园邑二百家,长丞奉守如法”【《汉书·外戚传·孝昭上官皇后传》卷九十七[上],第3959页】,符合皇帝岳父母的丧仪。上官桀、上官安被杀以后,他们也被葬在茂陵东边,应该和敬夫人在一起,因为那里是皇帝原来赐予上官氏的茔地,其地望在茂陵最东边,毗邻平陵陵区。由于上官桀、上官安犯法被诛,尽管他们可以入葬原来茔地,但不能享受达官显贵们的待遇。为此,孝昭上官皇后派自己的奴婢为其祖父和父亲守墓。今霍光墓以东,地面上已不见古墓封土。这或许由于当时上官桀、上官安起冢较小,加之年代久远,因此坟丘湮没,已难寻觅。除了朝廷的达官显贵、皇亲国戚陪葬茂陵,一些大官和豪富也竟相争取死后葬在茂陵附近,如京兆尹曹氏和巨豪原涉。
(三)霍去病墓石刻
茂陵众多陪葬墓中,霍去病墓最重要,而它又以其墓前雄伟的成组石刻而闻名于世,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。霍去病墓石刻包括圆雕的“马踏匈奴”、跃马和卧牛,线雕与圆雕相结合的伏虎、卧象、野人、石蛙和石鱼等。霍去病墓石刻出于官府工匠之手。在已发现的霍去病墓石刻作品中,有两件分别刻着“左司空”官署名称和“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”的文字题铭。左司空属于少府属官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:“少府,秦官,掌山海池泽之税,以给供养,有六丞。属官有……左弋,居室,甘泉居室,左右司空……。”秦汉时代的砖瓦上,常见左、右司空的陶文戳印。霍去病墓石刻中的“左司空”刻铭,说明左司空兼造石刻。霍去病墓石刻为左司空所造。
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,霍去病墓石刻有的置于墓前(坟墓以南),如石刻“马踏匈奴”。大多数置于象征祁连山的坟丘上。
霍去病墓石刻反映的历史内容,是相当丰富的。下面扼要介绍。“马踏匈奴”为霍去病石刻群的主像,石雕通高168厘米,长190厘米,宽48厘米。作者运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手段,塑造了一人一马,概括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功绩。石马与真马大小相近,昂首站立,肌肉丰满,尾长拖地。马腹下面仰卧一人,头对马嘴,两颊胡须稍长,面容狰狞,两足上曲,手持凶器,垂死挣扎。造型生动逼真,寓意深远。跃马,高150厘米,长240厘米,宽85厘米。跃马的后腿与后身跪在地上,前腿跃起,动态表情比较强烈,力量含蓄。这件作品线雕和形体配合一致,层次处理明显。卧马,高114厘米,长260厘米,宽73厘米。马躯健壮,姿态生动。马头稍左偏,右前腿稍曲,双目注视前方,再现了以骑兵为主体的西汉军队抗击匈奴的英姿。伏虎,高84厘米,长200厘米,宽60厘米。匠师选用了不规则的波浪式起伏的石料,利用石块的粗糙自然面,运用线、体相扭的造型手法,把凶猛、桀骜不驯的“虎性”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伏虎背部,由虎头一直到虎尾,构图结构紧密,中线清楚,头颈和胸腔连成一体。虎尾倒卷,置于背上。虎身斑纹异常生动,显得更有“虎威”。虎在我国古代是威武的化身,汉宣帝视南郡获白虎以为宝。《风俗通义》也说:“虎者,阳物,百兽之长也,能执搏挫锐,噬食鬼魅。”又说:“罔象畏虎与柏,故墓立虎与柏。”以虎守墓,防止妖食人肝,相传早在远古的帝喾时代就有了这种习俗。考古发掘中,在商、周时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玉虎、石虎和铜虎。战国时代的中山国王陵中葬有工艺高超的错金银铜虎。目前所知,我国古代,冢前列置石虎,以霍去病墓最早。东汉时代,墓上列置石虎者比以前显著增多。魏晋以后,大型陵墓列置石虎已相当普遍。据文献记载,武帝茂陵之中曾以活老虎随葬。以“虎”“镇墓”者称为“虎镇”,在汉墓发掘中这类遗物屡见不鲜。卧象,高58厘米,长189厘米,宽103厘米,石象雕刻着重于写实。象鼻搭在左前腿之外,身躯匍匐在地,匠师刀法秀丽、娴熟,造成象体平滑、温顺可爱的艺术效果。石猪,高56厘米,长163厘米,宽63厘米。形似现在的野猪,整体为蹲伏状。双耳较小,眼睛为三角形,头部雕琢相当精细。这可能是古代一种未完全驯化的家猪,或是当时的野猪。以猪随葬,始于远古。有的墓内置以整猪,也有的仅放猪头。墓内随葬猪的多少,或许象征死者生前财富的多少。猪也是古代祭祀的牲畜之一。霍去病墓上的石猪,恐怕都不具有上述意义,而可能是霍去病战争环境或当时社会生活的自然写照。
石鱼两件高60厘米,长114厘米,宽47厘米。匠师以精选的天然石料稍行加工,使之粗具鱼身外形,头部线条简洁明快,雕出嘴、眼的轮廓,看去犹如一条在水中时隐时现的活脱脱的游鱼。以鱼随葬,由来已久,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,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一直沿袭下来。贵族墓中随葬玉鱼,一般平民墓中则是陶鱼。武帝茂陵中也瘗藏有鱼。西汉时代,武帝开凿昆明池,池中养的鱼,专门有于祭祀诸陵。霍去病墓上的石鱼,应是作为祭品而设置的。石人,高210厘米,宽125厘米,厚94厘米。石人的头大于真人,眼与眉向上竖起;有身无腿,左臂余少半,缺手,有臂完整无缺;手置腹上,五指分开,手心向外。石人的整体犹如一件生动的漫画作品,轮廓基本保持了石料原来的卵状,雕刻技法属于不规则的去地阶梯型线雕,情感表现力比较突出。石雕的人与熊,高265厘米,宽172厘米,厚98厘米。石人头大、口阔,牙齿外露,头稍前俯,两肩耸起,左腿曲膝,左腿跪地,腰间系带,胸前两手抱一小熊欲食。小熊也不示弱,张口与人对咬。整个作品以线雕为主,运用扭曲的线条、夸张的手法,栩栩如地表现了人兽殊死搏斗的场面。浮雕的运用,增加了人与兽的质感。牯牛,长260厘米,宽160厘米,高(卧地)115厘米。石牛体壮,头较大,角前为圆形,背上刻有鞍鞯,跪在地上,口作反刍状,犹似耕作已毕,关中老黄牛的形象跃然于石上。整个作品,厚重圆润,线条清晰,动态自然。猛兽食羊,石刻长260厘米,宽210厘米,厚120厘米。这件石刻主要采用了高浮雕进行艺术处理,这对那种“四不象”的猛兽来说,有着特殊的表现力。猛兽方头、大口,兽角为很长的软角,身短腿长,两只前爪撕扭着小羊,小羊拼命挣扎。由于匠师选用了风化得比较厉害的石料,石雕的表面起伏较大,使得艺术效果更为强烈。霍去病墓前这组石刻,线雕、圆雕和浮雕运用得当,有的注意形态,有的突出神情,有形有神,形神兼备。看到这批石刻,眼前不由得浮现出祁连山古战场上抗击匈奴侵略的场面:那里有深山荒原,有凶猛野兽,险恶的自然环境越发反衬出西征将士们不畏艰难、英勇善战的精神。霍去病墓前这组大型石雕作品,在我国目前来说,是一批时间最早、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!从文献记载来看,坟墓列置石雕,似乎源远流长。上古时代的尧母庆都陵和尧陵之前均有石驼。“汴都(今河南开封)之南百里”的西周初年周公墓前竖立石人。周宣王墓前列置有石鼓、石人、猊、虎、羊、马等石刻。相传秦始皇陵上还有一对石麒麟,石刻高达一丈三尺。可惜上述记载,至今尚未得到考古实物的验证。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,不但秦及其以前的陵墓上未发现列置石雕,就是西汉十一座帝陵上,也没发现过一件西汉石刻。因此,我们认为,秦和西汉的帝陵上,可能未置石雕。
达官贵族墓上的石雕列置得似乎比帝陵早一些。从西汉中期开始,少数达官贵族的墓前出现了列置的石雕,除了霍去病墓,还有张骞墓。在其它少数地方,也曾发现了个别西汉时期的坟墓前列置了石雕,但都不会早于西汉中期。如山西安邑杜村西汉墓前的石虎,山东邹县城东匡庄古墓前的石人等。霍去病墓和张骞墓前列置我国最早的陵墓石刻,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。霍去病是征战西域的著名将军,张骞是通西域的著名外交活动家,西域是他们创造丰功伟绩的广阔舞台。两墓之前(或上)列置石刻,表明当时受了西域文化的某些影响,例如,近年在新疆地区调查、发掘的石人石棺墓文化遗迹,分布在北疆草原地区,如:阿勒太、富蕴、青河、哈巴河、吉木乃、布尔津、温泉等地,这些遗址的墓前有石人立像或立石,这类石人石棺墓的时代,早期可上溯到秦汉之际。霍去病墓上的巨石和目前的石人等,很可能就是作为西域文化中的杀人石而立的。在西域地区,一些墓前立有石人或巨石,它们往往表示战场的俘虏,以其装饰坟墓,让其服侍死者。显然,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像就含有类似的意义。当然,与新疆北境草原一带的石人石棺墓的石刻相比,霍去病墓石刻反映的历史内容更为深刻、广泛。霍去病墓的石刻,对以后我国历代陵墓石刻的影响是深远的,这主要表现在陵墓石刻的题材与组合方面。
如霍去病墓的石虎,实际上成了魏晋时代陵墓前石刻的辟邪前身,后者不过是虎(或狮)的异化体。至于达官贵族墓前列置石虎,沿袭的时代更长。
墓前列置石马,比其它石刻持续时间都长,扩及的范围都广。象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“六骏”,就与霍去病墓的石马主像寓意相近。
此外,以石人、石象等饰墓,亦为后代所仿效。霍去病墓石刻中的石人、石马和石虎等组合,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。
(四)阳信公主墓陪葬坑的考古发现
在茂陵陵园东司马门以东约2100米处,东司马道南侧,分布着东西并列的五座陪葬墓。其中最西面的一座,是这群陪葬墓中离茂陵最近的一座,也是这五座陪葬墓中现存封土最大的一座,封土底部南北长95米、东西宽64米、冢高22米。由于封土南端高大、北端低小,呈“羊头”状,所以当地群众称之为“羊头冢”。
根据墓南侧第一号陪葬坑中出土的刻记有“阳信家”铭文的18件铜器分析,此墓被认为是阳信长公主的墓葬。
阳信长公主是景帝和孝景王皇后的长女,汉武帝的姐姐。她始嫁于西汉王朝开国元勋曹参的后--平阳侯曹寿,卫青少年时还是他们家的奴仆。卫青地位显赫之后,“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,长公主问:‘列侯谁贤者?’ 左右皆言大将军。主笑曰:‘此出吾家,常骑从我,奈何?’左右曰:‘于今尊贵无比。’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,皇后言之,上乃诏青尚平阳主。”【《汉书·卫青传》卷五十五,第2490页】
卫青与阳信长公主成婚后,从《汉书·卫青传》记载来看,阳信长公主先卫青而亡,因此,卫青死后“与主合葬,起冢象庐山”。据西汉时代葬俗,达官显贵死后夫妇合葬,同茔不同穴。也就是说,夫妻合葬在同一茔地,但分别各筑一座坟墓。一般来说,当时这种夫妻距离,少者十几米。多者也不过一、二百米(当然,皇帝和皇后陵墓茔域大,两陵间距一般几百米。特殊者,如文帝霸陵与孝文窦皇后陵间距近两千米)。但是,今卫青墓与阳信长公主墓相距约1330米,他们的夫妻茔地不可能这么大。而且,其间有茂陵东司马道东西穿过,将二墓分置于神道南北两侧。再者,卫青墓与阳信长公主墓之间还有霍去病墓和金日磾墓。因此,不能把“羊头冢”和卫青墓看成“同茔不同穴”的夫妻合葬墓。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认为,很可能阳信长公主死后先葬于“羊头冢”,卫青死后,她又被迁葬于卫青墓附近,与之合葬。这种推测的根据,是在卫青墓东北50米处,经钻探发现一座大汉墓,墓穴东西长26米,南北长25米,深24米。该墓封土现已不复存在,前些年坟墓的封土还有部分残存,并有清代康熙年间立的石碑,碑文标识为霍去病墓。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《长安史迹考》一书中,据此石碑认为,此墓与其南面140米的霍去病墓,均为霍去病墓,可能其中一墓为衣冠冢。我们认为从此墓位置来看,它离卫青墓比霍去病墓更近。这就是说从茔域部局来看,它很可能与卫青墓在同一茔域。再者,在卫青墓附近,除了此墓和霍去病墓之外,其它陪葬墓都与其相距甚远,不会属于同一夫妻茔地。可见,只有此墓应为与卫青合葬的阳信长公主墓。
与卫青合葬的阳信长公主墓应为迁葬墓,其原墓应是“羊头冢”。“羊头冢”陪葬坑出土的大量“阳信家”刻铭铜器证明了这一点。
1981年,考古工作者对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进行了勘察,共发现了39座陪葬坑,发掘了其中的一座。陪葬坑主要分布在墓南和墓北。已发掘的陪葬坑在墓南60米,地下深3.2米,呈南北方向。北坑是个带过洞的方形洞穴坑室,平面呈“凸”字形,全长4.15米,其中坑口长1.2米,过洞长1.22米、宽0.85米,高0.8米。坑室南北2.45米,东西2.3米,高1.95米。坑室以木板封门。坑内器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边,铜器最多,其次有铁器、漆器、铅器、木器等。这些器物中,有实用器物,也有明器。在这4平方米的陪葬坑里,出土了230多件器物,其中鎏金铜马、鎏金鎏银竹节铜熏炉等物,无疑是当时最高封建统治阶层享用的宫廷器物,为皇太后赐给长公主的。这批物品,反映了西汉时代的最高工艺水平。
下面简介这些物品:
鎏金铜马:高62厘米,长76厘米。铜马昂首站立,张口,竖耳。马的肌肉和筋骨匀称合度,造型朴实稳重。鎏金鎏银铜熏炉:造型罕见的艺术瑰宝。熏炉通高58厘米,底径13.3厘米,口径9厘米,盖高6厘米。熏炉炉盖形如博山,透雕多层山峦,如之金银勾勒,给人一种云雾缭绕、恍若仙境之感。支撑炉体的是竹节形高柄,共五节,每节上竹叶枝杈。柄上端铸有三条蟠龙,龙头承托炉盘。龙身鎏金,龙爪鎏银,线条流畅活泼,形象生动自然。底座上透雕的两条蟠龙,翘首张口。此外,还有提链炉、温手炉、灯、钟、甗、甑、盆、匜、鼎、温酒器、斗、掉、铫、臼、虎镇等铜器。名贵的漆器,作工精细。车马器是随葬品中的大宗。出土的一辆小车和十匹小马,均为木质,表面涂漆。残留金属小车器、马饰等19种,计121件。上述陪葬坑及其出土的文物,为我们研究西汉的社会生活、帝王葬仪、工艺美术,提供了丰富、生动的实物资料。一个陪葬坑就出土了这么多随葬品,可以想见阳信长公主墓三十几座陪葬坑中随葬的珍贵物品数量之多!也不难想见,西汉封建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。
- 上一篇:上官家族七世祖上官桀等墓考察【计划】 2018/11/22
- 下一篇:上官傑墓地考察进入申报实施阶段 2018/10/17